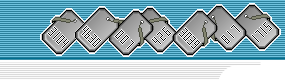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Hawke043481/5770527
阿敏當兵記(九)艱苦行軍
十一月底的某次收假,當晚上六點回到營地時,一個怪異之極的景象讓我無比震驚:帳棚全都不翼而飛,營地只剩一片空曠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莫非兵不用當了?
但是天下哪有這等好事?排長隨後出現,告訴我們,部隊移到新竹坪埔營區了。於是我們跟著他,坐公車到了新營區。這裡有營舍,不必再睡帳棚了,但我仍懷念野營的日子。
我是營部連醫務士,卻被連長「發配」到步兵連行軍。剛開始的課程是「連攻擊」,走的並不遠。白天上課,傍晚攻山頭;天黑之後分不清東西南北,一度迷失在叢林裡。有次在攻了兩次山頭後,就近在一個空屋裡吃晚飯,四周黑漆漆的,別有一番味道。在繁星點點的夜空下展開夜間攻擊,雖然無聊,但是差可慰藉。
不久我被調到尖兵連的尖兵伍(奇怪,是打算操死我嗎?),從營區走到新埔。其實也沒什麼,只是衣服會被汗水溼透。第二天,有人不行了,我和三連副連長把他送到空總。有次到十八尖山,寒流來襲,非常的冷。當時身體溼透,寒風吹來,差點冷死。走尖兵伍,說起來還是可以稍微炫燿的。只是有時候帶隊的長官走錯路,尖兵伍的弟兄往往是最倒楣的--我們要走最多冤枉路。
有次夜行軍,回到營區時聽說出事了--搜索排被一輛酒駕的汽車撞進去,許多弟兄受傷,最嚴重的是原住民阿貴;他的腿斷了,而他的腿曾經百公尺跑出十秒幾,台灣田徑史上前十傑…
辛苦和樂趣有時是相對的,當我們上「連防禦」的課程就是快樂的一天。我們總會找一個絕佳的地方隱蔽,既避風又掩人耳目。記得有一次,我們撥開草叢忽然發現一個「洞穴」,更妙的是裡面竟然有數本漫畫「風雲」。顯然英雄所見略同,這些是前人的「遺愛」。好事不僅止於此,當我們發現旁邊就有果樹,而那些獨立的果樹是農人不願登高採收,果子掉落一地任其腐爛的,每個人都欣喜若狂。數個人排成一列,將橘子、芭樂陸續送入「山洞」,然後一邊看漫畫,一邊享用。
所以,我們最喜歡的是防禦課。有時不見得有水果吃,因為長官曾告誡,不可以摘人家的水果。但有時候躺在玉米田裡睡覺,也是非常舒服的事。那種和大地合為一體,看著天空的感覺很棒。偶而「小蜜蜂」來了,就去買肉粽、飲料、巧克力來吃,吃飽了就繼續睡在田裡,這也是個重要的體驗--泥土並不髒。
一月初移防到新庄子,開始長行軍。有天不知走了多遠,走到深夜,大腿抽筋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那是剛開始走長距離,經驗還不足。我的大皮鞋裡掉進一顆米粒大小的石子,剛開始我想忽略它。因為部隊的行進速度是比強行軍還快的時速6公里多,只要你的鞋帶鬆了,彎腰下去綁好後再抬起頭,部隊已經在前面很遠的地方了。可是這是忽略不得的,雖然石子很小,但是長久的摩擦,令我脚底起泡。起泡之後還是得繼續走,然後水泡就磨破了。
一般人磨破水泡,定然呼痛。但是這對我們來說,尚不足為奇。因為我們知道水泡破了再繼續走,就會「泡中有泡」;有時脚底磨出了數個水泡,是謂「連環泡」。而最厲害的是「血泡」,有個弟兄脚後跟就磨出了半個拳頭大的血泡。當一天終了,回到營區洗完澡後,我親手以注射筒抽出他的血水,然後注入碘酒。
水泡破掉後還繼續磨它,會很疼痛。但是如果不走、裝病,該週就禁假;所以我還是咬牙走下去,只是落隊就難免。有個原住民弟兄看見我落隊,就用鄙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,叫道:「班長~」,我受不了這鳥氣,當這雙腳不是自己的,刻意用力去踩磨破的水泡,奮力往前走。結果天無絶人之路,這樣走了一陣子,脚底就痛的麻痺了;這下可好,我走起來勇猛精進,再不落隊。
記得那天深夜抵達一個國小,我們借宿他們禮堂,當雙腳休息時,感覺他們不斷在漲大。臨睡前我都不敢脫鞋子,最後是穿著大皮鞋睡到天亮;因為我曾試著脫襪子,但發現它已經和血肉黏在一起。
那陣子寒流頻頻來襲,我們受到嚴酷的考驗。第一次在雨中睡覺,是穿著雨衣,頭躺在樹下以便避雨。隨著在山裡過夜的次數增加,我們也越來越有經驗。剛開始,實在不曉得嚴冬的天氣,如何不靠帳棚睡袋在叢林裡過夜。後來知道標準的睡法是:脫下外套蓋身上,側著身體躺草地,如果仰或俯臥會因為土地傳上來的冷氣,而冷的受不了。但是側睡一會半身就痠痲了,所以必須換邊。整夜就是如此「輾轉反側」,直到天亮。根本沒人睡的著。
我的氣管不好,除了先天的遺傳外,當兵時冬天的露宿森林,也居功厥偉。到現在,我碰到冷空氣還會咳嗽。
這段期間,不知道日子是怎麼過的,自己怎麼熬過來的。常常想著,今天又走了多少路,自己都佩服。
http://www.wretch.cc/blog/Hawke043481/6187120
阿敏當兵記(十)之「美麗人生」
營測驗前夕的某次收假,老婆開車送我回營。到達新庄子時還有一點時間,我們坐在王爺公廟前聊天,不願就此分別,卻無力喚住時間的流逝。
營測的行軍,是下基地以來最苦的考驗。大約從凌晨四點半開始走到隔天凌晨三點半,整整二十三個小時。到了坪埔金山面,睡在戰鬥教練場。很冷,露水重,又沒東西可蓋,整夜幾乎沒睡。
第二天中午在苗栗新成國小吃飯,太陽露臉了,身心皆感到十分溫暖。躺在操場邊,睡到下午兩點半。當天走到了樹林裡,我用樹枝和雜草佈置了一個「繭」,躺在裡面可以仰望明月和滿天星斗。
營測結束的倒數第二天,我們邊走邊聊,言不及義;為的是忘卻疲勞。聊到有位弟兄自稱有陰陽眼。我們問他:「恐怖嗎?」,他說:「習慣了」。當晚我們睡在茶園旁的農舍前。農舍的門已毀損,看進去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。偏偏他的門戶又是洞開的,讓人總是覺得裡面有「什麼」會跳出來。
就是有一種愛戲謔的人,把別人的鋼盔丟到「黑洞」裡面,看著人家害怕的不敢進去拿,他就很得意。壞的是,這樣的把戲在瞬間流傳開來。更不幸的,我也是沒顧好鋼盔的人士之一。當我硬著頭皮走進屋裡,只隱約看到一堆舊農具,但是陰森森的怪怕人。
進過屋裡的,自然就是英雄,也有了豁免權;於是我得以安穩的睡個覺了。睡到中夜,突然變得好冷,感覺有團冷空氣直壓著我的身軀,讓我咳的醒過來。四周弟兄們睡的安沉。看看手錶,十一點;離天亮還早。但是我從那刻起,就沒睡好;恍惚中,聽到有人的吵雜聲。
第二天午飯休息時間,我們聚在一起,陰陽眼也在其中。我抱怨昨晚忽然很冷,害我沒睡多少。另一個我們營部連的上兵說:「是啊,昨天晚上十一點時,我也是冷的醒來…」。當下我只是覺得:原來這不是我過敏。不料陰陽眼說:「其實…昨晚有個阿伯一直坐在我們旁邊,我不敢講,怕大家嚇到…」。
營測最後一天,我們在雞舍旁的稻草堆,窩了一上午;直到發布基地訓結束。但是我躺著…竟有點依依不捨。回首走過的路,轉瞬間都已成過去。
營測雖告結束,但是我們一刻也不得閒。部隊要「機動」(整個部隊要坐火車),車輛都要「上鐵皮」(車輛也固定在沒有車廂的火車上)。我忙到凌晨,睡在悍馬車上。火車要啟動了,原本我想直接坐在悍馬車上,這樣可以暫時不受部隊管束。我可以看書看報,豈不甚美?後來想到,我可不願意對著悍馬車窗,在疾馳的火車上灑尿…而作罷。
搞了一整天,旣沒效率又無聊。坐上3:30pm.的火車,我和二連的排副搭「守車」(看守裝備),不舒適又很吵。到宜蘭,吃碗麵,打個電話。然後「下鐵皮」,又是弄到凌晨。
當兵絕對不是浪費時間(某些單位)。因為有許許多多的狀況,可以將你磨練成一個鐵人。
例如:除夕前一天,照著我呈的假單,換好了便服,結果放假名單卻沒有我。難道權力的迷人之處,就是可以任意玩弄人嗎?大年初一踢正步。它磨練的不是體力,而是脾氣。如果你曾在這樣的時節幹過這樣的事,則工作上再苦,都能甘之如飴。我沒有抱怨,只是感到自己有點荒謬。
年初一晩,留守的眾人問連長可不可以看錄影帶,連長說不准,自己卻跑到二連看。十點正,連長要我們準時就寢。有人去廁所,有人還沒睡,他就發飆,將全連集合。有個弟兄喝了酒,被他重重踹一腳。當蹲的蹲,跪的跪,被恐嚇的夠了後大家才上床。將要入睡之際,又傳來全連集合聲。
原來連長要我們看那個喝酒的弟兄被手腳綑綁,口中塞襪子。頓時我腦海中浮現的是納粹的集中營,和共黨的恐怖統治。不過,當時的情況,我也只能讓自己成為一個麻木的人罷了。
年初二以及初三,大家在連長的淫威之下,連電視也不大敢看。整天就是洗帳棚。我和幾個志願役士官苦中作樂,倒也不甚厭煩。
就寢時,躺在床上算日子;稍息之後,還剩199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