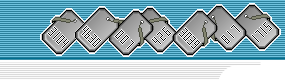勇者憤怒,抽刃向更强者。
怯者憤怒,却抽刃向更弱者。
還好我已經很很久沒看書了(咦?
拒買有什麼難,事實上這一年來你買了幾本書XD
先置板凳
這塊我先觀望觀望一下
在有結果前
等對方說明 保留
讓列車開一會
先不上車
帶什麼風向
先拔草(抓)測風向
等聲明
欸 公關會來洗地嗎 明天這篇還在嗎
希望有後續
通常都是幹幾聲 過一個禮拜就忘光
人的記憶是有限的,過陣子就沒人在意
協商就是想要少給嘛!
人家當事人都選錢少方案 外人還是閉嘴
大家可以回家了啦
所以2條路
1是博客來多付錢贏風向
2是付本來就該付的錢 不虧
謎之聲:是你不拿的喔 !
多拿一毛錢 會被網友打成貪婪
兩個方案就是陷阱,拿了優待就打貪婪勞工開失智列車
連加碼賠償都沒有 就是吃人夠夠
還用這種道德輿論壓力 逼他不敢多拿怕被說貪
被和解吼
再怎麼算也沒用,人家還很感謝公司
要你們看戲的鄉民被再鬧
律師都解除委任,怎麼算都沒用
[blackjack的blog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]
博客來「假承攬真僱傭」可恥卻有用,台灣真的在乎?
從外籍看護、漁工沒有勞基法,
郭o嗆只要合法血汗工廠沒不好談起
博客來是統一集團的
按照當時地溝油味全是頂新集團的,旗下所有東西都要抵制但是大家有可能抵制7-11嗎?
哈哈不可能啦
還有康是美、黑貓宅急便等等
提供的「清潔服務合約書」心頭一驚
,因為從上班內容來看,阿姨受到博客來高度監督,屬於「僱傭」關係,
但公司和她簽的
卻是「承攬」契約,
如今阿姨丟了工作,退休金、資遣費也領不到。
被要求打卡上下班,工作時間受到博客來嚴格管控,
打掃範圍也依博客來指示,
在在顯示她受到博客來高度指揮監督,是非常標準的「僱傭」關係。
應該幫阿姨保勞健保,提撥退休金,
更要在非自願性解僱發生時,給付預告工資及資遣費。
還是有國民年金可以領啊
保全或清潔工都用這種合約
現在承攬合約都是給清潔公司過水,實際指揮
看貼出來的合約,博客來不敢寫工時,因為寫了就是雇用
這麼大的公司都敢這樣你就知道全台灣多少
有在公司管過的人都知道一定是這樣簽比較划算
當初一堆舊制在第19年被資遣
一個打掃阿桑你要多懂她自己簽的是什麼?
就算懂,有什麼議約能力?
現在承攬都要跟人力公司簽,人力公司負責員工的勞健保
不然人力公司怎麼雨後春筍
其實沒有所謂的「勞保退休金」
正確的說法是「勞保老年給付」(跟「勞工退休金」是兩種不同的制度)
「勞保老年給付」是一種在職社會保險,是勞工在工作期間繳納的勞保保費,等到符合請領條件時,便可向勞保局提出申請。
給付方式可分為
老年年金給付(月領)、
老年一次金給付(一次領)、
一次請領老年給付
3 種。
各大企業(X)
政府帶頭(O)
政府都帶頭搞一年一聘
政府自己一堆勞務承攬
這種事情公家機關尤其是學校一堆
公務機關學校之類助理不是勞工,
幾年前就吵過自己翻新聞,當時一堆機關首長學校教授被調查
獄政社福也一堆承攬契約喔 政府就是最大慣老闆
政府一堆合署機關的清潔人員、工友之類的不都這樣玩,
還有每年精簡砍到不到最低工資,每天來整天變成每天來半天
國營單位掃地阿姨也都承攬 合約
勞動部自己下面就一堆派遣的啊
除了本身派遣的業務之外 還要分擔一堆別人的業務
醫院不就一堆打卡完再回來上班的操作
某醫學中心讓員工超時加班的罰款是兩萬台幣
-
應該很多人還不知道,
這種僱傭合約,博客來法務完全站得住腳
照法律是可以完全一分一毫不用給額外退休金(如同船員)
台灣賺到翻掉的海運公司,都是這種合約,
台灣很多要進口的東西都是這些默默無名的船員辛苦載回來,
結果也沒什麼太多保障,
海運公司都是這樣對待個人的
海運業也是普遍使用,所以才有幾十個月年終跟船員完全無關(領不到)
就是因為簽僱傭合約,簽多少領多少,公司賺再多也領不 到額外年終
前陣子才有中鋼退休的發現根本沒多少保險金在跟公司打官司中
-
自然人承攬,本來就是已經含勞健保
公家單位都可以了,記得是某人的發明
,萬年承攬一堆
那公務機關一堆人都可以去告
公機關自然人承攬也是要打卡上下班啊!
公司舊制退休金,二十幾年的勞健保追償,
還有因為沒投保勞保導致的勞保退休金損失,算一算大概300萬,
公司一定是想方設法拿個三十來萬開始找麻煩逼人和解,
尤其阿姨不識字,沒想到博客來狠成這樣一毛錢不給就要攆人走
(正常一點的公司會拿個幾十萬騙走人)
製造業大公司為了規避這種,還會另外成立ABC三家勞務派遣,
今年簽A明年簽B後年簽C公司,
不只沒退休金,每年年資都重頭計算,加薪也沒這些人的份,特休一天都不給你
勞委會居然都沒有說話,還鼓勵派遣
當初就勞委會一直跟大家說這制度多好多好
後來就進化成自然人個人承攬,都是從公務機關開始
每個契約都長的不一樣 名目也不同
就認定說公務機關 就也是同類型的假承攬真僱佣
現在隨便Google兩份區公所的合約上面寫的很明都是僱佣
外傳和解金額達100萬元,詳細金額及細節不方便透露。
博客來提出優於勞基法及符合勞基法的和解金額兩個方案,
李姓清潔工選擇符合勞基法的金額,不願意多拿一塊錢。
不接受就是等著訴訟好幾年 反正大公司能耗



管仁健觀點》清潔婦與博客來的爭議有「圓滿落幕」嗎?
https://newtalk.tw/news/view/2022-12-26/850249
「慢一點,等一等,經過大腦」
這十多年來,從督割事件與假灣生回家事件,每當社會上出現一些讓鄉民憤慨的新聞時,
本魯總是苦口婆心的規勸大家,務必牢記鍵盤小五郎管大的十字箴言:
「慢一點,等一等,經過大腦」。
要解除委任才能「圓滿落幕」嗎?
但清潔婦與博客來的爭議真的「圓滿落幕」了嗎?
究竟是法律戰能讓博客來火速低頭?
還是輿論戰能?
腦筋清楚一點的鄉民們,應該都有定論。
律師不見得只能幫委託人打官司,也可以幫委託人談和解吧?
自稱不識字的清潔婦,就算要與博客來和解,也不用解除律師委任,
讓原本委任的律師與博客來委任的律師,雙方的律師來洽商和解,不也可以「圓滿落幕」嗎?
但這是正常人的思維,不是中山狼的吃人模式。
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,
因此還是請鄉民們冷靜。
面對重大社會事件,務必牢記鍵盤小五郎管大的十字箴言:
「慢一點,等一等,經過大腦」
「薛文龍悔娶河東吼,賈迎春誤嫁中山狼。」
這是《紅樓夢》第79回的回目,賈迎春是12金釵裡的第7位,也就是男主角賈寶玉的堂姊。
賈迎春雖然漂亮,也善於下棋,但生性懦弱怕事,因此被稱為「二木頭」
賈迎春在處世為人上,一向只知退讓,任人欺侮。
父親賈赦欠了孫家五千兩銀子,還不出來就把她嫁給孫家少爺孫紹祖。
但孫紹祖為人粗暴,性格卑劣,好色好賭又酗酒,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全都遭他姦淫。
賈迎春婚後初次回娘家,淚流滿面向長輩哭訴,賈寶玉也求父親賈政讓迎春留在大觀園。
但按大戶人家的規矩,婚後留在娘家會遭人閒言閒語,
最後還是讓孫家的人把賈迎春接了回去。
果然賈迎春到了孫家不滿1年,就被渣男老公凌虐致死。
或許有鄉民會疑惑,孫紹祖就是個渣男,為何《紅樓夢》會稱他是「中山狼」?
中山狼是指戰國時代,
東郭先生要去中山國,路上遇到一隻被獵人追趕的狼,心生憐憫就將牠藏在自己書袋裡。
但是等到獵人一走,東郭先生剛把中山狼從書袋裡放出來,
牠卻張牙舞爪的說:
「東郭先生既然做好事救了我的命,現在我餓極了,你就再做一次好事,讓我吃掉你吧!」
說完中山狼就撲向一直在痛罵「忘恩負義」的東郭先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