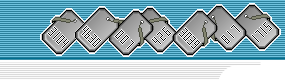一篇好文章。 轉載
http://www.worldjournal.com/3188 ... =%E8%89%BA%E6%96%87
排附排附•吃飯散步
■王正方
我在金門服役官拜陸軍少尉副排長,單位是陸軍9404兵工補給連,駐紮於太武山後的一個隱蔽處,距離那座老天主堂不遠。兵工補給連設有幾間小倉庫,主要是調配供應汽車、戰車的相關零件等。
少尉是最低階的軍官,兩邊肩上各戴著一條窄窄的銅槓子。我本是大學畢業生到部隊裡混個一年半的少爺預備軍官,每日歸心似箭,連長不敢付以重任,叫我 負責「轉撥站」,接到貨隨即轉送到他處而已。每天早晚點名、唱軍歌、呼口號、等吃三頓飯。早餐每人分個饅頭,多吃一個饅頭服役的日子就少一天,數饅頭的日 子過得特別慢。
第一天到連上報到,天氣悶熱,只穿著圓領衫同幾個新來的充員兵有說有笑的。過來一位滿臉鬍子渣、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漢,沒頭沒腦地對著我們破口大罵。 聽了一會兒,是在罵我們死老百姓充員兵不懂規矩,見到軍官不敬禮。他愈說愈氣,用食指在肩帶上比了一比,說:「見到了這個沒有,是什麼?這是國家頒的軍 階,俺從戰場上拚老命掙來的,你們就敢不尊重?」其實他肩帶上沒戴著那根小黃槓槓,制服久經日曬,肩帶上有一條顏色較深的印子而已。大家立正聽訓十分鐘。
晚點名時,連長介紹新報到的王副排長,然後叫我接任本周的執行官。我來了個標準敬禮,向後轉的動作乾淨俐落,口令喊得短促有力,呼口號、領唱〈反攻 反攻大陸去〉那首歌,嗓音嘹亮。第二天用完早餐,罵人的北方大漢走了過來,一臉和善咧著大嘴說:「王排附,敝姓楊,也在這兒幹個排附。」
不「罵」不相識,他名叫楊威,字象震,現年三十三歲,甘肅蘭州人,口音挺怪。以後慢慢同他混熟了,都喜歡下象棋,楊威的棋路既狠又毒。他對自己的名 字甚不滿意,因為「威」字與「萎」的發音太接近,可是連上弟兄就要叫他陽痿。祖父取的名字,怎能更改?在老家找了拆字先生起了個字:象震,取威震四象的意 思,讀起來也鏗鏘響亮,我就一直稱呼他象震兄。
他小時候在老家念過幾年書,因為家裡窮才去當兵,候補文書士,就是連長的秘書,那個連長不認識幾個字兒。幾經戰亂分到這個連上來,因為沒讀過陸軍官 校,在升遷上很吃癟。熬了好多年,通過考試才從准尉升少尉,准尉是更低的官階,已經取消了。象震兄性格直率,我們相處得不錯,經常一塊散步、下棋、抽菸、 拉屎、聊天。老士官們見到我們這兩個芝麻官兒,就喊:「排附排附,吃飯散步!」
連上的士官長,多是大陸來台的老兵,國共內戰戰敗被收編,又送往朝鮮戰場,被美軍俘虜,爭取來台灣再編入部隊。早年大陸的部隊沒有副排長這個職位,有「營附」、「連附」、「排附」等,是長官安插小舅子的閒差,「排附」當然最沒地位。
金門服役的生活枯燥,星期天上午連上派卡車送大家去縣城,下午接回來。當時的金門縣城只有兩條街,多是雜貨店鋪。象震兄每個星期天必定邀我去縣城,主要是去看某雜貨店的美女店員。
那位標致的南國佳麗,大眼睛、身材豐滿,很多人為她傾倒。這小姐仗著點姿色就跩得厲害,對三、四十歲的阿兵哥根本不假顏色,像我這樣二十出頭的小夥 子,有時候她還肯理會一下,象震兄就鼓動我上前搭訕,他在一旁看著也開心。我又能怎麼樣,不過就是買肥皂牙膏什麼的,詢問總共多少錢?小姐腦筋快會心算, 幾秒鐘就說出錢數來。象震兄在一旁低聲讚嘆:「你看她那小帳兒算得挺清楚。」我們耗在店裡不走,小姐無聊地哼起流行曲子來:「藍紅(南風)吹來暖洋 洋……。」象震兄又禁不住的低聲說:「你聽她的小歌兒唱得多好聽!」一直沒進展,我們還是逢星期天就去那兒報到。
另一個節目是去縣城某國民小學看電影,如果放的是外國片,象震兄一定要我陪著。那個年月的西片,片子上帶有中文字幕的不多,這時我就要不停地講解, 否則他跟不上劇情。看電影的人多,小學禮堂擠滿了人,去晚了就得在後排站在板凳上看。象震兄叼著根菸捲,往往極投入地被劇情所吸引,口水從嘴邊慢慢流下來 也沒察覺,他說:「媽了個逼的還真緊張!」
喝高粱酒是星期天必須做的事。通常我作東買幾包花生米、豆乾、蠶豆,一瓶58度的金門高粱,找個陰涼的地方,三、五個人輪流對著酒瓶喝,一下子就幹掉一瓶。面紅耳赤地批評罵街,我們的指導員總是頭一個被罵,那人實在太討厭了。
金門算是前線,管制得特別嚴格。來往信件指導員都要先拆開來看,然後才發到受信人手中。老士官們沒什麼信,像我這種充員官兵的信最多。正與關係危在 旦夕的女友魚雁頻繁,每封信都讓官拜陸軍上尉的高指導員先睹為快,他比我先知道最新發展。知道別人的隱私也就罷了,高上尉還喜歡當著許多人,面帶玄機地對 我說:「王副排長,你那朋友我看對你不怎麼樣了呀!」然後他呵呵乾笑,我憋住一肚子窩囊,只有在星期天喝高粱的時刻開罵。
還是「雙日停火」的時代,對岸每逢單日就朝著金門發射宣傳炮彈。多數從福建圍頭打過來,先是一聲低音悶炸,不多久就聽見炮彈劃空的呼嘯,愈來愈尖 銳,然後炮彈在空中炸開,是一種清脆的爆裂巨響,大量的宣傳紙片紛紛飄下。按照規定,一聽見炮響,弟兄們就該趕快躲進附近的防空洞去。象震他們是老江湖 了,豎起耳朵傾聽一下炮彈劃空的呼嘯聲,就能夠聞音辨位,大約知道炮彈落在哪個方向,距離有多遠。
有一次空爆宣傳彈的聲音特別響,好像在我們頭頂上炸開來。象震使了個眼色,說:「走,我們去找傳單。」兩人就朝著天主堂跑,果然在教堂附近有不少宣 傳紙片飄散著。揀了幾張宣傳單子,上面印的都是繁體字呢!沿著原路回去,炮彈還在此起彼落地響著。就看見指導員扠著腰在路口守望,他瞪起眼睛大吼:「你們 是出來看煙火的呀!要是叫炮彈片子砸死了,往後還能吃口糧嗎?可好,隊上原來也不缺你們兩個廢物蛋子。」
「宣傳彈砸不死人的。」象震頂了一句,可惹火了高上尉,他叫囂著:「你比我還懂?匪他們詭計多端,要是中間夾著打一枚實彈過來,怎麼著,要俺給你們收屍?……」一口氣站著罵了二十分鐘。
我不自覺地摸了摸口袋,發出紙張摩擦的聲音。指導員狐疑地看過來,他說:「兜兒裡藏了什麼東西?」我掏出那張傳單來,象震兄機警,馬上說:「王排附正要上繳。」指導員提高了嗓門,聲音尖銳:「匿藏匪諜,與匪同罪。你知道私藏匪的宣傳品是啥罪過嗎?這裡是前線……。」
嚇得我渾身顫抖,這事可不能鬧大了,那年月前線隨便槍斃個人不算一回事的。象震兄拚命替我開脫講情,指導員一把奪過宣傳單,一眼也沒看就放在褲袋裡。他又講了成篇的反共八股,幸好晚飯的時間到了。這事後來並沒有追究下去,我深自慶幸。
這麼一個極可惡的人,象震兄還覺得高指導員除了嘴巴刻薄不饒人之外,人算不錯:「指導員沒有治你的罪呀!」「你這純粹就是鄉愿!」我批評這種爛好人的心態不可取。象震兄認為我年輕氣盛,不懂人世間的事情,現在的部隊比以前講道理多了。
「從前俺在西北地方部隊,那才叫野蠻哩!連長的權柄很大,隨便槍斃人。」「你槍斃過人?」「沒有,但是我見過。逃兵被逮回來,二句話不說拉出去就蹦 了。都是同鄉,犯了軍紀可是一點情面也不講。」「有次連上會計的帳不清楚,大概是連長那份錢算少了,關了他三天禁閉,氣還沒消,叫衛兵用麻繩反綁起會計的 手,兩腳懸空吊在房梁上用馬鞭子抽,抽一鞭子就罵一句髒話。然後甩門出去,叫俺看住這個賊。連長剛出門俺馬上把會計放下來,他頭上的汗像黃豆粒子那麼大地 淌著,再吊下去兩隻胳臂就廢了。」
「後來呢?」「後來會計還幹會計,他們是小同鄉,有親戚關係,自己人,不然他找誰替他弄錢?在秦嶺那場戰役,連長、會計,連上總共有六十多人陣亡,連長的帳也不用算了。」
我差點捅大婁子。約老楊一塊去蹲茅坑,廁所髒臭到無法形容,找個伴蹲在那兒抽菸閒聊,比較好打發。還是個軍官用的廁所,糞坑之間有一塊矮木板隔起 來,蹲著齜牙咧嘴的當兒,好歹彼此還有點隱私。那天伙房不知給大家吃了什麼,弄得人人後期作業困難,聊了半天抽了三支菸還沒完畢,蹲得腿腳發麻。我說: 「象震兄呀!你說我們這位指導員……。」
象震兄一陣窸窸窣窣從旁邊的坑竄出來,彎著腰在我面前搖手,要我禁聲,一面指著不遠的一個坑,他褲子沒穿上,大屌兒在胯下晃悠著,我馬上了解到那邊蹲著的就是指導員。事畢整理好服裝走過去,看見指導員正愁眉苦臉地蹲著奮鬥,我立正行軍禮:「指導員好!」
象震兄從來不光顧軍中樂園,這一點我很佩服。部隊裡都是青壯年體內荷爾蒙分泌旺盛的雄性動物,生活單調無聊,工作又特別無趣,怎麼能不想去幹那事 兒?像我這種數饅頭的預備軍官,心有所屬,寂寞了就勤寫情書寄回台灣,被人甩了也好默默地體驗失戀中的淒美,痛苦總會有個盡頭。連上的老弟兄們,他們又該 怎麼自處?
連上還有位蘭州老鄉,姓白;綽號白嫖客,人高馬大,一有機會就往軍中樂園跑。白嫖客喜歡找象震兄聊天,兩人說的蘭州官話非常快速,後來我可以聽懂 七、八成,聊的都是軍中樂園的事。白嫖客吹他有多厲害,一上去就是下不來,老經驗的都不斷求饒,白嫖客說:「俺還沒出水不算!」就這樣子經常白嫖。他不時 帶來最新消息,新來個妹妹如何如何,引起連上一陣騷動。
象震兄真有那麼大的定力,還是他行蹤詭密,像我們指導員似的,一個人偷偷地去幹那事,「單嫖雙賭」嘛!但是我覺得他不是那種人。象震兄跟我講過他的「家裡」,北方人管自己的老婆叫「家裡」。十五歲那年他在老家娶了媳婦,媳婦比他大五歲。
「她大你五歲,二十的姑娘比十五歲的愣小子懂事吧!」「這個自然囉!頭一天睡在一起還挺不習慣的,一個月下來俺啥也不會,啥也沒幹,就覺得她的氣味 特別好聞,摟著她睡不用說有多舒坦啦!她那個氣味……也沒法子說清楚咧!」「後來呢?」「後來俺爹就催著快點生個孫子,我問爹;那要咱整呢?爹先罵我蠢, 然後教我如何如何,這才上了軌道。」「你他媽的還真是你爹的好孩子哩!生了孩子沒有?」「生了個胖小子,好漂亮好漂亮的胖小子。」
象震兄每次說起那胖小子的時候,目光就有點呆滯聲音變得喑啞,不自覺重複地說:「好漂亮好漂亮的胖小子!」他對妻兒的懷念總帶有歉疚,因為那時年紀 太輕,受不了小孩的吵鬧,他會惡聲咒罵老婆和孩子。老楊還打過他媳婦:「俺的狗性子急,一吵架就亂摔東西,有一次把菜刀摔了過去,還好是刀背砸到她腿上, 磕出一個像花生粒那麼大的疤。俺媳婦長得才俊呢!臉上有幾顆白麻子。」
胖小子生下來不到兩年,家裡過不下去了,象震兄補上了那個文書士,隨著部隊東奔西走的,頭兩年還寫信回去,寄點錢給家裡。只接到兩封代書寫來的家信,夾著一張媳婦的情書,以後兵荒馬亂,多少年了,再也沒有老家的消息。
「不是說你媳婦不識字嗎?她會寫情書給你?」「她畫了一張圖來,裡面有好多意思。」「她的畫你還留著?」「唉!留著就好了,打仗的時候逃命都來不及,什麼都丟光了。」
沉默了許久,象震幽幽地說:「有幅畫俺記得好清楚,她用眉筆畫了一頭大象,象鼻子捲著一把菜刀,砍死了一頭鵝。」「什麼意思?」「象殺鵝啦!她想煞我了。」
幾百隻饅頭終於有數完的一天,連上安排了吉普車,送我去料羅灣搭船回台灣。象震陪著我等船,下午有一艘大型登陸艇緩緩開進來,等登陸艇下完貨,這一 批充員官兵整好隊伍,準備涉水登船。象震兄塞了兩瓶金門高粱58在我手裡,我說:「你們留著喝嘛!」「帶上,聽說這酒在台灣不好買。」
登陸艇的艙門大開,像一頭巨獸的血盆大口,一陣擁擠,我扛著行李拎著金門高粱,往那張大嘴衝過去,頃刻間海水就淹到我的胸口。
聽見象震兄在身後喊:「反攻大陸的時候再回來數饅頭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