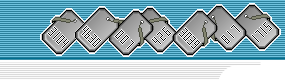引用:
原文由 小瓜呆 於 2012-05-31 17:37 發表
管仁健《你不知道的台灣》系列第2本《校園奇案》...
【四六事件】他們的制服,與那場大逮捕 - 方格子
https://vocus.cc/article/624c16d8fd89780001a66073
vocus.cc › 台灣服飾誌
2022年4月5日 · 四月六號時,配槍的士兵進入臺大校園與師範學院拘捕學生,許多學生與教職員受到處分與判刑。這件事和「制服」,有什麼關係呢?

說到「制服」引起的騷動,你會想到什麼?
也許是2013年台南女中的「脫褲」抗議行動,
或是這幾年「制服存廢」而引出的論戰。
但早在改革制服的呼聲出現之前
,1940年代的戰後初期就曾因為制服產生了一系列騷動。
混亂的開端:戰爭時期的中華民國制服
民國十八年時,
教育部公布《學生制服規程圖樣》
同年國民政府也發布訓令,
要求「凡是中等以上的學生,一律穿著制服,以示整齊」
當時的大學生穿什麼呢?
從《學生制服規程圖樣》的附錄中,
可以看見,民國十八年的大學制服是有些類似日本立領西裝「詰襟」的樣式,
冬季穿著黑色,
夏季穿著白色;
頭頂戴著四方帽;
天冷時加上一件雙排扣大衣。
民國十八年《學生制服規程圖樣》
1930年代
進入中日戰爭時期,
為了因應戰爭時的體制,
民國三十一年
國民政府增修《高中以上學校軍事管理辦法》
重新規定高中與大學生的制服:
「實施軍事管理之學校,全體學生無論在校內校外一律穿著制服」
在這份辦法裡,也重新規定了樣式:
「衣褲採用中山裝…
夏季深黃色或灰色,
冬季灰色或黑色…」
也就是在這時,大學生制服改成中山裝。
民國三十五年時
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》發布《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制服製備辦法》
更明確指定臺灣的高中以上學生制服為:
「國產布中山裝,
夏季深黃色,
冬季黑色」
因此深黃色的「中山裝」成為戰後初期臺灣的大學生制服,
直到民國三十九年才有所改變。
遍地的「国民服」制服
在民國三十五年時,
除了公布高中以上學生制服以外,
還有另一條訓令也值得注意:
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代電:學生不得穿軍服》
「各地學生著草黃色軍服…時有發現,殊易紊亂服制,有損軍容」
為了能讓未學過國語的臺灣人也能遵守規定,這份訓令甚至還頒佈日文版本。
1939年時,
日本頒布《學校生徒兒童服裝統制ニ關スル件》
統一全臺中小學學生的穿著,
並因應中日戰爭的戰時體制,
整體服裝設計類似於陸軍備服協會頒布的《国民服令》
並打上綁腿;
在戰爭時期,
日本政府還研發出一系列的「国民服」做為民間的戰時推廣穿著,
不只學生,民眾也會穿著與制服相似的国民服。
不管是「国民服」或是學生制服,顏色大多因為戰爭被統一為「國防色」
也就是如今的卡其色。
出事啦!學生制服與軍服的大亂鬥!

民國38年4月6日
才一改過往語氣,頒布一挑新的命令,由「警務處」發布:
「台灣省警務處代電:
事由:
奉電以非軍人穿着已蓋「限期染色」戳記之軍服,應沒收繳送等因希知照。」
同年5月3日,教育廳又頒布了一則新的命令:
「教育部令敕學生禁穿軍服或與軍服式樣及顏色相同之服裝
轉希遵照」
「查近來因各地學生隨意穿着軍服,
致少數不肖之徒竟冒充學生或軍人,聚眾生事,不特擾亂治安…
學生應按規定穿着制服便衣,
不得穿着軍服或與軍服式樣及顏色相同之服裝,
以免與人混淆不清…。」
國民政府的陸軍制服,與「中山裝」學生制服,基本上長的一模一樣。
顏色上的差別呢?
陸軍制服是「草黃色」
學生制服是「深黃色」
都是屬於戰爭時期的卡其色。
不能說是有點像,只能說是幾乎一模一樣。
所以可以想像,
當學生包圍警局、舉行遊行與抗議時,總是會讓人疑惑一下這群人究竟是軍人,還是學生?
更甚至是我們可以想像一下,當軍警進入校園時那個畫面:
一群穿著卡其色制服的人,進入到一群穿著卡其色制服的學校,大家的制服都長得很像。
那個畫面說有多混亂,就有多混亂。
別忘了,這起事件裡面還有另外一群人,就是原來就讀於日治時期高校的本省學生們。
他們當時的制服若沒有因為民國35年的取締「限期染色」而替換掉,
就會保持著戰時日本政府頒布的類似國防色(卡其色)「国民服」的學生制服。
也就是說,當軍警進入省立師範學院的校園時,還會碰上另外一群臺北高中的學生。
在這場搜捕行動裡,不管是「軍人」、「師範學院」、「臺北高中」,大家穿的都很像。



民國三十九年,教育廳公布了新的命令:
「奉省府核本省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制服變通辦法」
「查,近以保安司令部奉令取締非軍人穿着軍服,
對於高中以上學校學生之制服應加以規定,以資識別。
本廳兼顧法令與與學生實際困難起見,
擬具本省公私立高中以上學校學生制服變通辦法…。」
國民政府想出的變通的辦法是:
一、學生如果穿著深黃色制服,
要在左胸口別上有學校名稱、學生名字的三角形小布條。
二、今年的秋季開學時,所有高中以上男學生的制服一律改成灰色。
三、如果穿深黃色制服,並且有別三小型小布條的話,我們就不取締你。
-
在這之後,大學生的制服由「深黃色」,改成了「灰色」
這樣灰色的制服也成為了一代人的回憶。